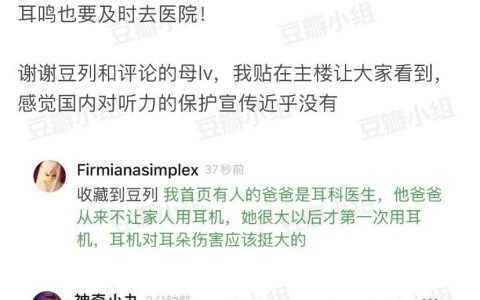王朔能瞧得上的人没几个,但他曾经说:
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我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1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生在北京,原籍重庆江津。阿城的父亲叫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建国后曾在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
阿城在家中行二,上边有一个哥哥,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诸事不争,唯独吃肉,寸土不让。阿城吃起肉来,眼放绿光。小时候时家里穷,偶尔吃顿肉,会把一块肉平均分成五块,肉上拴线,熟了以后,大家找自己的线,分头拎着吃。
每次他吃完自己的,就开始盯着妹妹的,他总觉得妹妹一个女孩儿,肯定吃不了那块肉,应该能给他留点。
阿城的童年过得不太顺,三岁时就染上了肺结核。八岁时,父亲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电影的锣鼓》,随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级别从10级降到了17级,去了渤海边的劳改农场管厕所。
他们一家留在北京,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了振兴巷6号一个大杂院。母亲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同时还供着姥姥和正在上大学的舅舅,实在拮据,有时要靠卖书维持生计。
阿城初中时去练游泳。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就没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渊潭去游野湖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阿城做什么都没资格了,在学校被边缘化,没有尊严,不能去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只能去琉璃厂翻翻古书,看看字画儿,研究研究古玩。
反倒因祸得福,学了不少东西。阿城说他永远感谢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新中国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虽然便宜,但还是一本也买不起,就站着看。店里的伙计都很好,从不管他,要是有的书搁得高了,还会帮他够下来。他的启蒙,是在旧书店完成的。
阿城在琉璃厂待得很舒服,那种舒服,他还记得,「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燥。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他每天混在玉、瓷器、字画儿、印章这些曾经的生活方式里,伴着啸音,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学杂。后来他与人聊天,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已经不一样了。琉璃厂是阿城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份,他后来总不喜欢工农兵文艺,也与琉璃厂有关。
2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城十七岁,已然一身本领,却背着「黑五类子女」这口黑锅翻不了身。1968年,家里有门路的都留城了,他只能下乡,辗转山西、内蒙、云南三地,前后十一年。
在山西雁北桑乾河边的一个村子里,阿城遇到一个叫运来的高三学生,也是北京的,长得像关公,他对阿城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这句话,阿城说他一直受用到现在。
阿城在云南插队时还是有过一些快活时光的。当年阿城身体不好,干不了粗重农活,组织便安排他到10分场的子弟学校去教书。语数外,体美劳,没有不教的。
每天晚上,大伙儿都会聚到阿城的屋里,听他边抽烟边讲故事,讲《基督山伯爵》,讲《悲惨世界》,讲《老高头》。煤油灯下,遍地人头。讲到关键处,阿城就会停下来休息,顺便吊他们,这时就会有人迅速递上一支春城烟,同时再来一个人赶紧往茶缸子里倒水。一切就绪,阿城继续。
当时,阿城的女友罗丹同在农场教书,也是北京知青。从云南建设兵团回来的人,会传一些阿城的轶闻。比如他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个音响,用来听BBC的古典音乐广播。他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听音乐,可以不吃不喝听上一天。阿城还穿过边境,到对面的山上看过美国和平队放阿波罗登月纪录片。
阿城爱音乐远胜文学,他曾带着三十倍放大镜专门飞到广州,只为了在著名的淘街买一个能读取完整信息的唱针呈超椭圆型的唱头。,
1979年,阿城回到了北京。刚回去时,阿城只痴楞楞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后来,他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谋了个活儿,随后又到公司的《世界图书》杂志当「以工代干」的美术编辑。
罗丹1973年先回了北京,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当了老师。罗丹一直在等阿城,经常去看他的父母。
那一年,阿城的父亲钟惦棐正式平反,出山任了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兼书记处书记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母亲也恢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十八岁那年,钟惦棐对阿城说了一句话:「咱们是朋友了。」得知父亲要被平反的那天晚上,阿城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1979年,阿城开始帮着父亲撰写《电影美学》。抽空还给北岛、芒克等人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画插图。同年,他也在和黄锐说、艾未未等人一起办「星星美展」,展览破了中国美术馆的纪录,参观人数超过十万人。
后来,阿城和罗丹结婚了。借了同事一间小屋暂住,就在北京美术公司对面,是60年代的简易居民楼,12平米左右,设施简陋,生活不便,吃饭得用煤油炉。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名画。小屋未能久住,主人要用房,阿城夫妇搬到了定福庄二外的办公室,继续暂住。
再后来,他俩又搬到了德胜门内大街临街一个大杂院里的两间小东屋,屋子有些年头了,白天和晚上一样昏暗,柱子、椽子散发着霉气,但好歹算是落听了,这是阿城在单位轮换分房所得,14平米。接着,罗丹回娘家生了孩子,是个男孩儿。
阿城爱子,溢于言表:
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都吃光。带他去吃冷食,三根冰棍几分钟便吞下去了,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还要。我就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
3
阿城写《棋王》那两天,诗人芒克正好在他家借宿。天气有点冷,阿城的小东屋紧挨马路,他们经常天没亮就被无数只羊蹄子敲马路的声音敲醒,芒克不知何故非要半夜赶羊。
阿城告诉他:「这是从塞外赶来的羊,专供北京人吃的,正直奔屠宰场。也只有这段时间才放这些羊进城,不影响交通。你瞧瞧人有多坏,要吃人家吧,还让人家大老远的自个儿把肉给背来。」说完转身又睡了。
1984年7月,阿城的小说《棋王》发表在了《上海文学》七月刊,瞬间引爆全国。阿城的小东屋每天应接不暇,接待全国各地各路文学刊物前来求稿的编辑,有时一天能来好几拨,一拨能来好几次,几天光景竟喝掉五斤茶叶。
《棋王》一开始其实是投给了《北京文学》,被退了稿才给的《上海文学》。阿城说《棋王》是用三四天时间写出来的,但罗丹回忆,要比三四天更短一些。
据阿城自己说,王一生不是凭空蹦出来的,在生活中确有原型,但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凑成的。主要原型是他在云南景洪农场下乡时,一个叫何连生的北京知青,那人在景洪下过棋,把当地下棋的全镇了。
《棋王》最早的结局其实不是现在这样,现在的结局是《上海文学》嫌调子太灰,让改的。原先的结局阿城在动笔前给几个朋友讲过(大意):
多年以后,「我」到云南出差,听说王一生已经调到了体委,成了专业棋手,「我」刚进云南棋院,就看见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出来。「我」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儿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
一次,又有人来约稿,看到桌上放着一个大陶瓷碟作烟灰缸用,烟头如山。那人开口问:「抽这么多烟,胸口憋得慌不憋得慌?」阿城悠然答:「不抽就憋得慌。」
二人一笑。那人除了稿子,还要一份小传,阿城说我过一天给你。第二天,阿城交了小传:
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
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1979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
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像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作家止庵感慨道:「阿城是第一个让我感到中文之美的作家。」
「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晋也五体投地:「阿城的文字在我读过的中国作家中文字最为俭省、凝练,我认为克制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因此,王朔、冯唐与阿城中间隔着一条宽阔的长安街,而且还没有斑马线。」
陈丹青说得最明了:阿城是「作家里的作家」。
过了一年,罗丹被组织安排到二外的姊妹学校日本京都大学去教一年汉语,走前她还在担心:「走上一年,这屋里又该下不去脚了。」
1985年,阿城已经从单位辞职了,和朋友一起办了一个公司,一通折腾,也没赚到什么钱。那两年,阿城又写了一些小说,《树王》给了《中国作家》,《孩子王》发在了《人民文学》。还有一些短篇,散乱给了一些杂志,后来收到了《遍地风流》里。
他计划是要写八个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拳王》、《车王》、《钻王》等,都是写知青题材和农场生活。他爸更是平添一趣,连小说集的名字都起好了,八王倒置,就叫《王八集》。阿城后来把《车王》写出来了,投给了《钟山》,赶上寸劲儿,居然寄丢了,导致至今都没人见过车王的轱辘长什么样。
再后来一个阶段,阿城的创作好像已经变成了慈善写作。他有选择地给一些地方小刊物投一些别处不易看到的稿子。他说,一个短篇可以让一个借用编辑从县城调到省城,让他们夫妻团圆,成全好事。
这个时期,阿城就已经向朋友表述过他对文学的腻烦了。阿城认为文学只是一种偶尔为之的生存手段,他说他靠手艺来吃饭,靠手艺吃饭的人不能把自己钉在一个固定的点上累死。
三王陆续发表后,来阿城小屋的人就更多了。阿城最喜欢吃面条,自己在家几乎顿顿吃面,主要是挂面。朋友们经常见他门也不锁,托着一斤挂面满目春潮,大步进院。
全国各地的人都向阿城涌来,阿城以面待客,最高创下过一天下面十六次的纪录。有时他离家几天,也会在自家窗上留字:「出门了,几日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
但这种热闹阿城并不喜欢,他插队回京后其实一直不适应:
这个城市就是容不下你。你十多年不在这个城里,没有人脉,哪去找工作?我一个快30岁的人,(刚回去那会儿)什么都没有,在父母家搭个行军床,每个月还要父母给你一块钱两块钱零花钱。耻辱啊!你在这个城市耻辱感特别强,因为你不能独立。
音乐绘画小说诗歌,解决的不是安身问题。整天聊天,那是二流子。到美国去,我一看,这地方好,打工不必认识人,好活。你知道在北京,在中国没有社会关系很难生活下去。一个人如果认识什么人,那是他的资源,可没有关系的话,就跟那个民工一样。
有记者采访阿城,觉得当时《棋王》那么轰动,他在中国也可以活得很好。阿城完全不这么看:
你必须有关系,还是这个问题。靠那个书其实养活不了自己。作家是一回事,出书是一回事,能不能用它养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王朔可以,他的发行量可以养活他,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畅销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畅销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
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把作家两个字印在名片上,因为对别人很不礼貌,那意思就是说:我是要饭的。
4
1985年到1986年间,阿城去了两次美国。第一次去是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
1979年之后的十年间,白先勇、萧乾、艾青、王安忆、张贤亮、冯骥才、汪曾祺、北岛、刘索拉等许多中国作家都参加过这个计划。
阿城去了美国以后发现那边不需要关系,完全不是人情社会,你不需要认识人,就能找到活儿,比北京好活。第二次再去美国,阿城就留下了。
阿城刚到美国时住过一段时间房车,给人刷过墙,送过外卖,什么都干。阿城从来没有瞧不上体力劳动,他的动手能力极强。他是好厨子,也是好木匠,能打全套结婚家具,能修护难度极高的明式家具,他最早横越美国的二千美元旅费就是靠木匠手艺赚来的。
后来有记者一脸不解地问:「你以前在美国主要靠打工维持生计?」他回呛道:「我在美国打了很多份工,主要是刷墙。刷墙不用动脑子。我为什么非要去做那些费脑子的工作?」
阿城也不是一直待在美国,他经常满世界转。1992年,阿城去了趟威尼斯,受邀旅居、闲逛。之前一个意大利人翻译了《棋王》,看疯了一群意大利人。意大利每年都会从世界范围内选一名作家在威尼斯住三个月,然后交一部作品,先出意大利文,再出本国文字。
阿城之前的上一个受邀者是诺贝尔奖得主,流亡美国的俄国诗人布罗茨基。阿城后来交的,就是《威尼斯日记》。
后来在美国收入多了,阿城搬到了一个两居公寓。国内的朋友去拜访他,还是面条款待,那会儿罗丹和儿子还没来。阿城还倒腾了一阵子仿古家具,战绩一般。后来就开始教钢琴,好久不见的友人听说他在教钢琴,大惊,从没听说他学过钢琴。
阿城嘬了口面汤严肃地说:「要教得教高级班的,准备参加国际比赛的。那会儿人家不需要你在技术上指导。只需要咱们从艺术修养上面、格调理解和演绎方面,从心理承受能力方面加以调教和指导。这绝对是教高级班的活儿。比赛前的最后点拨,这当然便宜不了。一年有几茬,就足够养家糊口了。」
友人追着问:「要是学生不够呢?」阿城又嘬了一大口面汤:「我攒车啊。在美国玩儿车啊,不需要技术。只需要逻辑概念。比如说:
你到汽车坟场找一辆三十年代破烂不堪的德国车。咱不一定非得奔驰,大众就行。你几十块钱或一两百块买下来,拉回家。然后,去大众汽车的代理商行,订购一本那个年头那个型号大众车的汽车手册。内容非常详实。
你按图索骥,先把所有的橡胶件、易损件全套买下来。回去一点点拆开,一点点换上。然后把气缸拆下来,拉到修里部几百块钱就搪了缸、试了车。你再把气缸拉回来,按照图纸要求一点点装上。其他部分什么刹车、底盘系统啦,变速器啦,电路、油路啦,一点一滴,一步步仔细地来。最后一辆崭新的老爷车,就在你手底下就诞生了。
当然,别忘了,喷漆可别舍不得花钱,铜活儿一定得锃光瓦亮,古董车最讲究品相。你花了心血,花了时间,还玩得舒服。你一共花了两、三千美元的本钱,至少还不卖他两万以上?一年玩一部,就足够你踏踏儿地活着。
那几年,阿城家里到处都流散着汽油味,零乱扔着各种汽车配件。阿城通过自学,亲手组装了六七部大众的古董甲壳虫卖钱,最后一部拉风至极,是一辆红色敞篷,很多人要买,最高有人开价十四万美金,他都没舍得卖。
阿城开着那辆车上街,遇到红灯停下来,经常会有人上来问卖不卖。阿城一律摇头,不卖。
挣钱之余,阿城也一直在写,「写作一定要用母语。我基本每天都在写,有时一两个小时,有时七八个小时。写作是一门工艺,像绘画一样,讲究心眼一致。你要是长期不写,手就不听话了。」写到得意处,他会给自己炒两个菜,下一碗最爱的面条。吃完再冲个热水澡,舒舒服服往床上一躺。
阿城1992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了,在洛杉矶期间他没少敲字,可惜倒了血霉,有一天电脑坏了,所有东西全丢了,后来他就写得少了。
写是写得少了,但却一直在说。王朔1997年住洛杉矶期间,周末经常去阿城那个小圈子的聚会玩,听他神侃。王朔自己说:「各地风土人情,没他不懂的,什么左道偏门都知道,有鼻子有眼儿,嗨得一塌糊涂,极其增智益寿。」
王朔问过聚会中的一个人,他老这么说有重复么,那人说她听了十年了,没一夜说得重样儿。
陈丹青一语中的:「阿城是天下第一聊天高手。」
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感受是:
与阿城聊天,无论什么话题,他都可以接过去,且聊得机敏,聊出味道。偶尔有接不上的地方,也只是把脑袋仰在那儿笑着吸两口烟,等低头掸烟灰时,则马上又会把断裂的地方续接得天衣无缝。聊完后告一段落,你兴致甚浓地对他说,今天聊得很愉快。他会很得意地说,我和别人聊天,大家都感觉愉快。
王安忆认为阿城是一个有清谈风格的人,阿城觉得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东西,海阔天空地聊天。
另据作家陈村观察,座中若有悦目之女子,阿城的发挥便愈加精彩,听者真能达到生不愿封万户侯的境界。
在美国,欢欣中也有糟心。阿城遇过一回贼,有一次旅游归来,一开门,傻了,全家被搬的只剩一个床垫。最让阿城心头渗血的是上百张珍藏了数十年的经典CD。他开始自己破案,他转遍了自家街区的所有音像店,翻那些二手CD架。
终于,他找到了盖有自己印章的CD,于是报了警。最终,顺藤摸瓜,所有CD都回来了。当年他在北京住德内大街时因为老不锁门,也遭过一次贼,那次没这么苦,他还能笑。他笑着说贼偷走了夹在《金瓶梅》里的存折,却没拿走《金瓶梅》。
5
1998年开始,阿城频繁回国,主要是去上海,他妹妹在那儿。2000年以后,阿城彻底回国,回了北京,住在回龙观。
记者去采访他,他说他现在的一部分收入是靠卖照片,人家要什么他拍什么。他有很多设备,有一台哈苏903相机,配一个38毫米广角镜头,外置旁轴取景器,还有七八台七八十岁的老柯达相机,还有一台16毫米电影机,都是他在美国地摊上得的。
当年帮《今天》画插图时,他跟编辑徐晓说:「我这个人好色。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
那段儿时间,阿城计划从保定进一台织布机回来织布,还想在回龙观东边弄一亩地,盖一个大棚,一半做工作室,用来做石版画,另一半种东西,把他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稀罕种子种进去。
其实阿城后来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来自影视行业,毕竟赚得多。当年他就说过,「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孩子也有嘴。靠写小说挣钱太苦。小至个人,大至中国,衣食是一个绝顶大的问题,先要吃饱,再谈其它。」
其实阿城很早就开始玩电影了,1986年他就和谢晋一起做了《芙蓉镇》的编剧,1992年他又和胡金铨一起写了《画皮之阴阳法王》的剧本。后来他还做了电视剧《贞观之治》和电影《吴清源》的编剧。
他自己的几个小说也被拍成了电影,《棋王》拍了两版,香港严浩一版,大陆滕文骥一版。《孩子王》给了陈凯歌。2005年,阿城还担任了第六十二届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最近一部编剧作品是侯孝贤的《聂隐娘》。
滕文骥当年想拍《棋王》,但死活联系不上阿城。有一次得知阿城从美国回来,造访香港,赶紧打电话过去,那边没有半点兴奋,只是急着说:「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吧,电话费太贵了。」等他从香港回来,见滕文骥的第一句话就是:「香港的米饭好吃,不用就菜。」
阿城对吃很讲究。陈晓卿说,阿城特别喜欢吃湘菜,他每次吃湘菜和别人不一样,他一定要选一个最靠近厨房的位置,他认为湘菜吃的是锅气,离锅灶越近,你比别人花得钱就越值。
画家刘小东请阿城到家里吃饭,阿城也很挑剔,他说「吃肉,盘子要热」。陈村回忆,阿城食相庄严,目不斜视,吃饱放下碗筷,抽烟,不再动筷。
阿城的酒量也很惊人。有一年,他拉着芒克跑到河北一个县城,说要在那儿办一个窑厂,烧些艺术陶瓷。县里几个头头出面接待,事儿还没谈,先开吃。阿城把一整瓶老白干全倒进一个大缸子里,菜没吃一口,酒已经见底了。那帮头头惊了,眼珠子憋得溜圆。后来,这事也没谈成。
阿城白酒可以,但黄酒不行。他第一次喝黄酒是在1984年文学圈的「杭州会议」,那也是他第一次见陈村。那晚他有点嗨,频频举杯,一杯一杯地干。陈村问他喝没喝过这东西,他说没有,像汽水一样,好喝。陈村告诉他黄酒性子慢,也会坑人。阿城还是继续干,和为他「改错别字」的《棋王》责编干。散席后,阿城不省人事,被抬上了楼,扔到床上。那次以后,他再不喝黄酒。
6
日久天长,阿城在尘世已经化作了一个传说。有一次陈村在机场遇上他,他给陈村掏了颗糖吃,说自己当了电影美工,要去外地刷墙。
他当年和侯孝贤合作《海上花》,干的就是美术指导。阿城自己说,他这个美术指导就是帮侯孝贤买东西,到各个旧货摊,潘家园什么的,买《海上花》那个年代用的煤油灯之类的,现在的道具做不出来。买完东西,就算完成任务了。但不能离开剧组,侯孝贤随时有事要问他。
有一天他正在组里的房间看书,侯孝贤召唤他赶紧去现场,他到了以后,侯孝贤说要在棚里拍下雪,但这雪花不对,飘的太假。阿城看了一眼,说我知道了。
然后爬到棚顶跟撒雪花的人说,把那些纸都先使劲拽一拽,拽松了,然后再撕,那个纸的密度就变了。再往下扔的时候,飘的速度就慢了。侯孝贤一看,对了,就它了。阿城说,那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说完,转身接着去看书了。
还有一次也是《海上花》。有一场戏是透过玻璃拍窗户里边。因为现场打光还是电灯光,煤油灯什么的都是道具。侯孝贤就觉得拍出来那个光不对,太硬了,就找阿城。阿城看了看,说拎桶水来。然后他就在那玻璃上刷了一层水,再回监视器看,有那层水那个光就柔了,显得有点儿油乎乎了。侯孝贤一看,又对了。
阿城的图书编辑杨葵最服的就是这个:
阿城的美术指导就是干这个。完全是一个杂家。那他这些东西是靠什么?生活经验,和对一件事情的体会能力。他能很快找到症结,更难得的是他有解决办法。他当知青也好、更早当狗仔子也好,总得要自己生存。所以他独立生存的能力是巨强的。他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各方面,还重视动手。
宁瀛有一次和査建英说:「应该有人扛一台摄像机每天跟拍阿城,一定是部特棒的片子。」
一次,杨葵在一家饭馆巧遇阿城,太久不见,杨葵蘸着寒暄打招呼:「怎么您老也在这儿啊!」阿城语冒寒气:「有谁规定我不能在这儿么?」杨葵一下就噎饱了。阿城很爱噎人,大概就是他的六面玲珑两面刺。
洪晃对第一次见到阿城,是在姜文家,那会她刚看完《威尼斯日记》,特崇拜阿城,特想上去搭话,但感觉阿城特不待见她。熬了半天,实在忍不住了:「阿城哥哥你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我呀?」阿城反问:「不跟你说话,就是不喜欢你啊?」洪晃一下也饱了。
阿城对朋友也是这样,会当面指出朋友的不对。刘小东说,「我说心里话,我不好意思当面请教阿城任何问题,因为我在他面前就是一个白痴。你不管和他有多熟,只要你说错一件事,他马上就指正你,他不给任何人留情面。他不会顺着你说的,他永远会告诉你一些应该的事情。」
画家朱新建和阿城是形影不离的酒肉朋友,据他回忆,有一次阿城从美国回来,朱新建跟他说:「二十年前,我在你家,给你看一篇我写的东西,你拿笔帮我改,一个字没添,杠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字。从此我突然就对写字这件事有了一些体会。」「是吗?」阿城一脸委屈,「我那么无耻?」
当然,大多数时候,阿城没刺,他对朋友极为仗义。2003到2004年,刘小东画完了两幅大作品《三峡大移民》和《三峡新移民》,要办一个展览,去找阿城帮他写一点东西,阿城说试试吧。结果,没过多久,阿城就拿出了十万字的文章给他,把整个三峡的历史讲了一遍。
还有一次在北京,阿城背着一个军用黄书包回来,朱新建问是什么,阿城带着几分得意打开给他看,满满一书包钱。那会儿还没有一百的票子,但就这一书包十块也让人看了很过瘾。
阿城说:「你拿一点去。」朱新建拒绝:「我干吗要你的钱。」阿城说:「这么多钱我一个人怎么用得完。」朱新建还是不要。后来朱建新跑到巴黎去混,实在手紧时写了一封信到美国,阿城收到信后,寄去了一千五百美元。
2000年左右,导演刘奋斗通过朋友结识了阿城,两人都爱聊天,持续见面,每周天天在一块吃饭。2003年,刘奋斗拍《绿帽子》,跟阿城开口,说能不能帮他来当监制。
阿城说,「你觉得用我的名字能帮到你,就用。」后来刘奋斗又问阿城能不能帮忙联系焦雄屏,因为他知道阿城跟侯孝贤他们关系很好,阿城马上打了电话,焦雄屏就来做了制片人。
确实,台湾文艺界聊起阿城就像在说一个神。「阿城是个难以被话语描述的文艺复兴人。他既能画画、拍照,也擅写小说、随笔、编电影剧本,还有烹调、修护家具、组装汽车等好手艺。阿城是小说家、文体家和生活家,不妨视他为坐拥世俗却清明谦冲的智人。」这是2003年台湾人介绍阿城时的话。
作家朱天心1986年生完谢海盟,坐月子时就在读阿城,她当时觉得世上有这样一本东西,她从此不用再写作了,就好好当妈妈吧。据她描述,那种感觉非常幸福:「你面前站着个终其一生都追赶不上的高手,你就好好当他的读者,放心去做另外一个自己吧。」张大春也说过:「早年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非常崇拜阿城。」
看起来阿城好像过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生活。但他自己说,「我喜欢和不读书的人来往,他们身上没有读书人的那股习气。」他平时来往的朋友来自三教九流,他交友的准则是,「对方有信用。」
阿城是喜欢烟火气的。他在台湾居留期间,侯孝贤安排他住木栅的安静山边,事后阿城说,下回能不能就让我住永和豆浆楼上。
7
一直以来,经常会有一些陌生的朋友到阿城家里去拜访他,有的只是为了能一睹风采,听他聊聊天。黄章晋第一次去阿城家时看到了一本大厚书,《中国古代气候研究》。
黄章晋自己说,他大部分时间里就像个鹌鹑一样,是个旁观者,但有幸插了五分钟的话。阿城不爱聊文学,即使你主动谈起文学,他也兴致寥寥。
阿城家里的陈设物品很多,很杂。地上零散堆放着石像、石碑,过道的长条案上摆着一套特别漂亮的五金工具,走廊尽头是一架很老的防空炮瞄望远镜和两台老式摄影机,另一侧条案上,整齐码着几排磨制的石器。到处都堆着成捆的书,多为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类,几乎没有文学类。书桌茶几上都是文物和矿石标本。
有一年,天井里还养了两只大乌鸡,阿城说这鸡是苗族巫师祭祀用的,他去贵州看苗绣,就带回来两只,养着每天看看。
可能只有阿城才配得上兴趣广泛这个词。摄影、绘画、音乐、装帧艺术,以及各种吃喝玩乐的技艺,他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他喜欢倪云林,八大山人,也喜欢毕加索,达利,喜欢意大利歌剧,也喜欢京剧和京韵大鼓。他最喜欢是还是中国民间的那些东西。泥塑、烧陶、傩戏面具、新绛剪纸、贵州苗民的绣衣,都是他珍贵的宝贝。
就像唐诺说的:「阿城是个好读书而且杂读书之人,但和我们这一代人大不相同的是,即便近乎手不释卷,但阿城通过文字的学习比例仍远比我们低。」
阿城是通才,是杂家。他的种种经历,常人都无法相比。丰富经历下淬炼出的通与杂,更是对同辈的时代级碾压。如黄章晋所言:「阿老他更像是一个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他的兴趣,知识构成,他的偏好,完完全全更像今天的人突然穿越到三十年前了,所以他在那个时代特别吓人。」
面对阿城,王朔也曾松了口气:「这个人对活着比对写文章重视,幸亏如此,给我们留下了活着的空间。」
来源: 马东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zhangzs.com/228049.html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