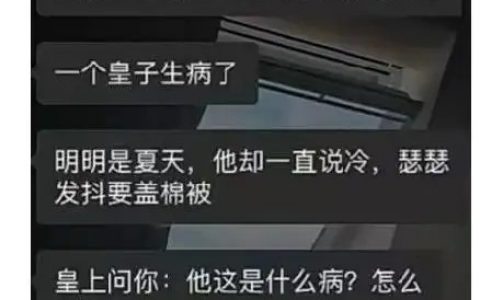1
最近有一个非常魔幻的新闻,日企造假造到了日料头上。
真是大水尿了龙王庙,尴尬又搞笑。
事情是这样的,前阵子日本有家搞生鲜批发的企业公开承认,他们一直把中国产的鳗鱼伪装成价格贵了几倍的日本爱知县鳗鱼拿来卖。
按新闻里的说法,这家企业起码从五年前就开始这么干了,关键是一直没人吃出差别,最后还是当地政府查发票的时候顺手发现的。
果然发票才是 YYDS。
日本鳗也叫河鳗、白鳝,本来就是中国的传统水产之一。
在日本买到的、挂着日本产标签的所谓日鳗,就算没有造假,也大概率是日本养鳗者从中国进口的鳗鱼苗养大的。
所以嘛,从关系来说,用中国产的鳗鱼,并不是违背祖宗的决定。
由于日本鳗鱼在上百年时间里进行的持续营销,中国鳗鱼在 C 端的知名度和品牌认可度上一直难以匹敌日本鳗鱼 —— 即使二者其实是一回事。
B 端卷死自己人,C 端打不过外人,后果就是坐视别人用经济手段掠夺原材料。
自己只能干最多的活、拿最少的钱,付出最大的代价。
以一条售价是中国鳗鱼三倍的日本鳗鱼举例,在最后的产品价格里,原料成本只占了非常小的比例。养殖和精加工带来了一小半价值,而大半利润,其实来自于 “日本鳗鱼” 的名号和相关品牌。
同样品质、甚至品质更优的中国鳗鱼,唯有换上日本产标签后才能身价倍增,看上去是一个嘲讽日本企业造假的笑话,但这本身也说明了中国鳗鱼在品牌上的弱势。
国鳗想要摆脱这个局面,就不能满足于做原料供应和贴牌代工。
原料供应是产业链的上游,但做好品牌和销售,才能成为价值链的上流。
产业链和价值链是两码事,上游和上流也是两码事。
谁是上游,谁做上流?
答案,藏在一个鳗鱼游戏之中。
这个游戏,要比鱿鱼游戏刺激多了。
2
日本人有 “吃鳗鱼、度苦夏” 的说法,在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里就提到过夏天应该吃鳗鱼。
但鳗鱼真正成为日本的流行食物,还要等到江户时代。
此时的日本刚刚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战乱,商品经济在难得的安定中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许多后来对现代日本影响深远的饮食习惯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比如蒲烧鳗鱼和鳗鱼盖饭的烹饪方法,以及要在夏季 “土用丑日” 吃鳗鱼的习惯。
简单说,就是只有当大家有钱消费了、有充足的物质和闲功夫试错了,才会去研究怎么烹饪更好吃,乃至形成各种特定的消费节日。
消费主义虽然难看。
但大家还有功夫搞消费主义的时候,其实说明日子还行。
虽然后来的研究表明,鳗鱼其实在冬天吃比较肥美,但夏天吃鳗鱼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一种传统。
即使平时不舍得买鳗鱼的家庭,在 “土用丑日” 也大概率会全家一起吃一顿鳗鱼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鳗鱼消费国,日本每年消费的鳗鱼数量超过十万吨,约占世界鳗鱼捕捞量的 70%——80%(此数据截至 2015 年)。
大量的市场需求,导致了长期的过度捕捞。
从上个世纪开始,日本的鳗鱼资源存量就在持续下降。
真的是,一滴都快没有了。
不光是日本鳗,欧洲鳗和美洲鳗也被人类吃得差不多了,几种主流的食用鳗鱼都相继进入了濒危行列。
鳗鱼濒危并不算一个新闻,很多年前世界各国的媒体就有报道。而且随着鳗鱼苗的捕获数据一年年下降,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媒体带上 “鳗鱼危机” 之类的关键词炒冷饭。
2007 年,欧洲鳗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 II,被要求严加管制相关贸易。
到 2013 年的时候,日本环境部将日本鳗也确立为濒危物种;
2014 年,国际保育联盟又将其列入濒危物种红皮书。
但是和 CITES 不同,这两类名录都不具备强制力,所以濒危归濒危,日本渔民依然在捕捞鳗鱼,日本水产企业也依然在生产和销售鳗鱼制品。
直到 2018 年 1 月,日本再次遇到了严重的鳗鱼荒。
在开渔禁 15 天内,全日本只捕捞到了几斤鳗鱼苗。
日本人这才有点慌,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好像真的捞不到自己的鳗鱼了。
完犊子了呀,真他娘西内。
其实有问题的从来不是野外捕捞,而是 “过度捕捞”。
即使人类不捕捞,新生的鳗鱼也会被自然界的捕食者吃掉一大部分。
如果计算好野生鳗鱼的产量,定好休渔期并严格遵守,鳗鱼资源是可以自然恢复的。
但问题就是,上个世纪的日本渔民简直是奔着让日本鳗断子绝孙去捕捞的。
他们把鳗鱼当鲸鱼干了。
结果在新世纪以后,日本鳗苗的捕获量就开始不断刷新历史最低记录,而鳗鱼制品也从日本人的日常饮食,变成了特定时期才舍得吃的 “奢侈食物”。
关键是,鳗鱼虽然可以人工养殖,但是不能人工繁育。
在繁育方面,鳗鱼堪称水产界第一作精。
偏偏这东西越作,它的肉就越好吃。
大家应该都听过鲑鱼洄游的故事,鲑鱼有溯河洄游的习性,上一代鲑鱼在淡水江河上游的溪河中产卵,幼鱼孵化后,会先在淡水中生活 2——3 年,然后再下海一两年,在海洋中生活、长大。
在即将性成熟的时候,这些鲑鱼就会逆流而上几千里,回到自己出生的溪河中产卵,一代代周而复始。
鲑鱼的繁育就已经够麻烦了,结果鳗鱼也有洄游习性,而且和鲑鱼的溯河洄游刚好相反,人家是降河洄游:
突出一个叛逆。
幼鳗会在淡水里长大,等到性成熟的时候再游到深海中产卵。
由于产卵和孵化的地点远离人类活动范围,鳗鱼在幼年期的生活细节成为了一个秘密。从具体的产卵地点,再到繁育、孵化所需的环境条件,人类长期以来都对此一无所知。
上世纪初,有欧洲学者发现欧洲鳗和美洲鳗会跨越大洋到百慕大附近的马尾藻海繁殖,离它们长大的淡水流域相距超过 5000 公里。
受此启发,日本学者一步步将日本鳗繁殖的地点往外推。1991 年,有人发现日本鳗的产卵地点竟然是在马里亚纳海沟附近,而更具体的定位,则要等到 2005 年才被确定。
在这种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人类对鳗鱼的人工繁育,就只能是不停地大胆猜想,大开脑洞,然后一步步试错、试错、再试错。
仅仅是如何让鳗鱼在人工环境下性成熟和产卵这一点,就难倒了学界几十年。
别说鳗鱼了,如何让人类多生孩子,全世界都没解决好这个问题呢。
1934 年,法国学者尝试过用人类孕妇的尿液来催化鳗鱼性成熟,结果发现这招对雄性鳗鱼的精巢成熟好使,却对雌性鳗鱼的卵巢成熟没什么作用。
就算有用,这个催化剂的获取渠道也过于不稳定了,总不能为了让鳗鱼怀孕,自己先怀个孕吧,福瑞控不是这么个意思。
上世纪 60 年代,日本学者给野外捕捉的雄性鳗鱼注射了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70 年代,法国和日本学者分别给野外捕捉的雌性鳗鱼注射了鲑鱼和鲤鱼的脑垂体提取物。
这两种注射都有效果,但蛋疼的是,就算用技术手段催化野生鳗鱼产卵了,这些卵也不会孵化。
于是日本的一支研究团队又优化了注射方式,比如在注射液中加入 DHP 和维生素 C/E。
鳗鱼好不容易产卵了,鱼卵也孵化出仔鱼了,这支研究团队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普通的饲料,仔鱼又根本不吃,最后全都把自己活活饿死了。
这孩子,从小就叛逆。
都到这一步了,这帮日本人觉得怎么都不能放弃了,一定要做到底。
2002 年,日本水产养殖研究所的田中秀树团队终于发现,用鲨鱼卵做原料可以配置出鳗鱼苗的饲料。
本来到这一步,算是大功告成了,他们笑了。
结果一算价格,他们哭了:
每条成活的鳗鱼苗成本达到了 100 万日元。
按当时的汇率算,也就是人民币七万五千元。
这可是 2002 年的七万五千元人民币,当时北京海淀的房价才 4000 元一平米。
技术上突破了,但是商业上算不过来,那就只能另谋出路了。
不然又得下海了。
哎?
我是不是说了又?
在日本学界研究日本鳗人工繁育技术的同时,日本企业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新的鳗苗来源。
这里就要提一下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日本鳗鱼分布情况了,所谓的日本鳗,也叫溪滑、白鳝,主要分布在日本北海道至菲律宾之间的西太平洋淡水域。
但除了这一块产地,也同样分布于在我国境内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沿岸及其江河。
查了查水产地图,日本水产企业两眼放光:
同样的鳗鱼苗,中国也有。
而且因为没有经过日本那样长期地、大规模地捕捞,中国的鳗鱼资源分布更广泛、储量更丰富。
关键是,此时的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
试图来大陆捡便宜的日本水产商,即将蜂拥而至。
3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住在汕头沿江海的居民们常常在淡水与咸水的交汇处成筐成篓地捞到一种外形奇特的小鱼。
它们其实是鳗鱼的幼鱼,由于身体细长,介于透明与不透明之间,犹如玻璃中藏了一条黑线,因此被称为鳗线。
这些鳗线本身无骨无肉,不符合中式餐饮习惯(西班牙人倒是喜欢吃幼鳗,结果这种吃法把欧洲鳗提前吃成了极度濒危物种)。
而鳗鱼的养殖条件又非常苛刻,对水域和环境都有很高的要求,缺乏专业技术的前提下很难养活。
既不喜欢吃,又没法养大,鳗线成为了鸡肋中的鸡肋。
当时的汕头人几乎不会去专门捕捞鳗苗,即使偶然捕获,往往也是带回去给鸡鸭当饲料。
如果鸭子会说话,他们会说。
嘎嘎嘎,好吃,嘎嘎嘎。
正因为没什么用,当地的鳗鱼资源反而得到了极好的保存。
直到七十年代初,一批日本商人来到了汕头,开始用 “高价” 收购这些鳗线,开出的价格达到每公斤(大约有 6500 尾鳗苗)数千元。
为什么 “高价” 要打引号,因为这些鳗苗被运到日本后,售价可以翻到十几倍。
同样的故事不只发生在汕头,从广东到福建,再到江苏的沿江海地区,都出现了大量日本水产企业的采购人员。
在外贸需求的刺激下,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个鳗鱼捕捞基地,向日本的鳗鱼养殖业源源不断地供应野生鳗苗。
日本鲤联为了掌握这些鳗鱼生产地的情况,甚至专门制作了日本版的 “中国鳗鱼生产基地图”。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种双赢 —— 原本没有太多经济效益的鳗鱼苗在日本商人手里转了一圈,就变成了价格高昂的 “软黄金”。
来自中国内地的大量鳗鱼苗,又给快要凉了的日本鳗鱼行业狠狠地续上了一口气。
但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精加工和高附加值的环节都掌握在日本手里,我国根本发展不起来自己的鳗鱼产业,只能做一个单纯的原料供应方。
若是长此以往,我国的鳗鱼产业必然会走上一条廉价出售资源的弯路。
直到某一天资源枯竭,然后被国际市场抛弃。
不能这样。
在当年那些鳗鱼捕捞基地中,江苏东台港曾经是相对得天独厚的那一个。
东台有着长达 80 公里的滩涂海岸线,是那时中国最大的捕鳗基地。
在东台港最巅峰的时期,中国出口的一半鳗鱼苗都是在这里捕捞起来的。
一直到 1986 年,东台港的鳗鱼苗年产量都还有 100 万尾。
但仅仅 11 年后,这个数字就只剩下了 1 万尾左右,下降比例,达到了恐怖的 99%。
东台港鳗鱼捕获量的衰落,不是因为外贸需求减少。正相反,恰恰是因为日本的鳗鱼苗缺口太大,外贸需求过于旺盛,才将这里积攒了几百年的野生鳗鱼资源吞噬得百不存一。
按理说,随着日本本土的鳗鱼苗捕获量一年不如一年,整个行业都靠我国出口的鳗鱼苗活着,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
但商业不讲道理。
或者说,这个体系讲的是另一套道理。
因为缺乏本国的鳗鱼养殖加工产业,我国的渔民在捕捞到鳗鱼苗后,唯一的选择就是等着被外国人收购,而且采购的大头还集中在日本水产商人这个群体手中。
没有选择权,就没有议价权。
日方如果想压价,只需要一句今年的采购量减半,或者一句明年不从你这里买了,就能把渔民拿捏得死死的。
关键是,野生鳗鱼苗是一种非常脆弱的自然资源。
一旦捕捞过度,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是会走向枯竭的。
这个过程有时会持续很久,有时只需要疯狂捕捞几十年。
很多事情太快了,不好。
4
幸运的是,我国有鳗鱼资源的地区不止一个,可以试错的道路也就不止一条。
1985 年,汕头成立了一家养鳗联合公司,简称鳗联。
鳗鱼产业本身并不复杂,和其他水产品一样,无非就是养殖、加工和销售。但围绕着这三个环节,足以形成一条复杂的产业链,带动多部门的人员就业和技术研发。
鳗苗的捕捞只是养殖环节的第一步,而且是附加值最少的一步,属于纯粹的祖宗赏饭、靠水吃水。
但只需要将这些鳗苗投入到鳗苗培育场中,培养成幼年鳗鱼,就可以多赚一笔。
而在将鳗苗培育成幼年鳗鱼的过程中,便会涉及到特定饲料的研发和相关产业。
如果能够将幼年鳗鱼养殖至成年,售价又会大幅度提高,而且养至成年的过程中,所需的饲料又有不同。
光是养殖这个环节,就可以养活一大批鳗苗捕捞户、鳗苗贸易商、鳗鱼养殖户和饲料生产商。
而汕头鳗联诞生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潮汕人不要再出卖鳗苗了,改为自己养殖鳗鱼。
大家不要跟钱过不去,尤其是赚日本人的钱。
在鳗联成立前,汕头早就有嗅觉灵敏的人修建了几百亩养鳗池,但这些养鳗池很快就荒废一空,布满水草水蛇。
个人养鳗,不但在技术上缺乏积累,把控不好养鳗池的水质、水温和饵料;
而且储备资金薄弱,采购方一搞事,资金链就要断裂;
最后还缺乏销售渠道,就算养出来了,也很难快速回笼资金,开始下一轮养鳗。
相比之下,卖鳗苗虽然上限低,但胜在几乎没有本钱,捞到多少就能赚多少,风险无限趋近于零。
因为风险都给了大自然。
当地人不傻,不需要等到鳗联来提醒,才知道养鳗比单纯的捕鳗赚钱。
问题是,养鳗不但是个技术活,更是一种风险投资。
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弱,玩不起这种大输大赢的游戏。
直到鳗联出现,一方面将分散在各地的养鳗场重新启用,由所有经营者分摊风险,并且承诺包销产品,将潮汕地区的渔民凝成了一股合力;
另一方面,又借助这股合力和日方谈判,通过补偿贸易的形式从日本引进了大量资金和较为先进的养鳗技术,1986 年的时候还引入了一条烤鳗生产线。
所谓的补偿贸易,就是你先把资金和技术给我,在一定期限内,我用产品(活鳗和烤鳗)或者劳务偿还给你。
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空手套白狼。
养殖户养大的这些活鳗鱼,会在加工环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活鳗和冻鳗出售,这里涉及到冷链技术和物流。
比起直接出售,附加值更高的是另一部分活鳗鱼。
它们会被送去精加工,制成烤鳗或者其他副产品,最后通过批发商、商场、超市或电商卖到消费者手中。
这些鳗鱼制品虽然会在货架上被分为日本鳗和中国鳗,但鳗苗的品种是一样的(日本鳗是从中国捕捞的),养殖技术和烤制技术也是一样的(中国鳗是从日本嫖的),味道当然也一模一样。
毕竟,如果一个东西叫声像鸭子,长得像鸭子,走路也像鸭子,那他特么就是鸭子。
嘎嘎嘎。
5
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鳗鱼产品凭借着不到日本鳗鱼三分之一的售价,以及不输于日本鳗鱼的口味,成功在日本市场立足。
这些鳗鱼以广东的汕头、台山、顺德等地为代表,因为自己就是原产地、中间商更少、人工更便宜,所以总成本要比日本鳗鱼低得多。
许多年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台山某食品公司的董事长依然会向记者回忆起那个如梦似幻的造富时代:
养殖 10 亩的鳗鱼,可以挣 150 万元,盖一栋别墅。
在这股鳗鱼浪潮中,大量养殖户因此致富,也诱惑了许多没有真正做好准备的人慕名涌入了这个行业。
规模的膨胀,并没有解决中国鳗鱼产业最大的硬伤:
缺乏自主品牌。
听起来有点魔幻,2021 年曝光的日本企业把中国鳗鱼当日本鳗鱼卖,实际上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了。
但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是中国的鳗鱼企业主动给日本鳗鱼品牌做代工。
没办法,中国鳗鱼的招牌,国内消费者不认,市场只能依赖出口;
出口到日本,日本消费者也不认,销售全靠经销商。
这就尴尬了。
实际上,从八十年代初期进入日本市场开始,中国鳗鱼一直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但日本的经销商只需要一压价,就会造成我国鳗鱼市场的剧烈恐慌和互相卷。
因为谁都不敢不降价,都怕竞争对手先降价。
那是鳗鱼产业在历史上非常尴尬的一个时期,产业体量虽然变大了,但都是一碰就倒的虚胖。
空有占有率,但是没主导权;
空有产值,但是没市场地位。
促使中国鳗鱼产业做出改变的,是接连发生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日本对中国鳗鱼产品的需求,那边的写字楼上跳楼归跳楼,我们这边该卖还是卖。
而且因为生前想吃最后一口鳗鱼饭,市场需求还更大了。
但日本经销商以经济形势不好为借口,趁机对中国鳗鱼产品压价,将出口价从每吨 14 万元压到了每吨 1.8 万元。
这砍价都不是打骨折。
这是片生鱼片呢。
养鳗鱼不像其他的实业,其他实业一般是投资多少亏多少,亏到没钱刚刚好。
但鳗鱼养殖业投进去 1000 万元,最后有可能亏 1500 万元。
为啥?
因为鳗鱼每天都要吃饲料,饲料价格还很贵,而且鳗鱼降价了,鳗鱼饲料不降价,因为同样的饲料还可以卖给其他水产养殖户,你不买,有的是人买。
亚洲金融危机变成了对鳗鱼的打击,当年靠养鳗鱼盖了别墅的广东养殖户,在亚洲金融危机里赔光了底裤,日本这一手危机转嫁,鳗鱼看了都想吐。
第二件事,是 2003 年日本对一批已经进入港口的中国烤鳗实施的 “命令检查” 恩诺沙星事件。
根据日本的食品安全法,日本有两种针对进口食品的检验检疫形式,一是检测检查,二是命令检查。
检测检查就是常规检疫流程,而命令检查则是强制性检查。
理论上,这是一种在发现进口食品频繁违反食品卫生法时,才会针对相应食品采取的特殊检查制度。检查内容以及对象会通过行政命令进行规定,并以命令形式指定有关检查机关进行检查。
对确定为命令检查的产品,需要进行批批检验,检查率达到 100%,费用由被检测企业承担。
在检查结果出来前,货物必须停留在港口,不允许办理入关手续。
恩诺沙星是当时国内水产养殖业广泛使用的兽用抗菌药,养鳗业自然也不例外。
这起事件有行业自身不够规范、养殖户缺少理论知识指导,导致药物滥用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受到中国烤鳗冲击的日本鳗鱼企业对中国鳗鱼发起的一场反击。
从 2002 年开始,日本就有一批鳗鱼行业组织在媒体上铺垫中国鳗鱼的喹诺酮类药物残留超标,但一直没有引起中国企业的重视,直到 2003 年的命令检查事件才真正将矛盾引爆。
在这起事件后,日本对中国出口的烤鳗增设了恩诺沙星残留检验项目,并设置了极低的检测标准,这就有点抛开剂量谈毒性的意思了。
据统计,2005 年中国烤鳗和活鳗出口金额比 2004 年减少近 15%,中国鳗鱼对日出口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而从 2006 年开始,日本又实行了严格的肯定列表制度,对外来鳗鱼产品(实际上有且只有中国向日本出口鳗鱼产品)设计了一百多道残留标准检测项目。
有研究发现,日本规定的药物残留限量每增加 10%,我国的烤鳗出口额就会减少 3.16%。本来当时中国鳗鱼的主要优势就是性价比,但在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后,中国的鳗鱼企业在出口前需要投入大量费用支付残留检测项目。
同时,这些花样百出的项目还会延长检疫周期,拖慢通关速度。很多时候,中国鳗鱼在到达日本市场时,就已经错过了 “土用丑日” 的鳗鱼销售高潮,只能吃到一些市场边角料。
而日本鳗鱼作为日本的 “国产货”,则无需此项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一来一去之间,中国鳗鱼的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就在无形中被抹平了。
市场中有看不见的手,狂伸中指。
除去复杂的检疫流程,日本还要求进口水产品在标签上注明名称、原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原材料名称、原材料产地、过敏源和养殖、冷冻情况,对于本国产水产则要求低很多。
为什么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日本企业手段那么粗糙都可以造假五年无人发现,除去中国鳗鱼和日本鳗鱼就是没区别以外,还因为日本对自己的 “国产鳗鱼” 几乎是免检状态。
有趣的是,从 2003 年的恩诺沙星、2005 年的孔雀石绿,再到 2006 年的肯定列表制度,这些以检疫为名的贸易壁垒,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抑制了中国鳗鱼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但却倒逼了我国的鳗鱼产业走向现代化和规范化。
在此之前,我国大部分鳗鱼养殖基地都是粗放式的养殖模式,并不具备追溯和记录生产、流通的能力,在饲养和用药上也全凭养殖户的个人经验,甚至是 “手感”。
你理解为玄学也可以。
从产品的综合质量来说,当时的中国鳗鱼确实不够稳定,盈利模式也主要靠低价走量。
结果日本对中国搞了一堆技术性贸易壁垒后,为了通过壁垒,我国各地的鳗鱼养殖户不得不脱离了游兵散勇和单打独斗状态,选择加入行会。
一方面,这些养殖户可以借助行会的力量完成技术改造;
另一方面,行会通过对养殖户和零散鳗鱼资源的收拢,也可以防止内卷,获得对日本市场的议价权。
日本的鳗鱼养殖产业虽然比我国内地有着超过一百年的先发优势,但到了这一时期,日本在养殖技术和检测标准方面已经被我国弯道超车。
中国的大型鳗鱼养殖基地基本普及水产品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体系(HACCP 体系)的时候,同时期的日本水产养殖还基本靠自觉性。
1995 年时,日本水产界曾因为卫生管理制度的缺失而被欧盟全面禁止输入,从那以后,日本鳗鱼就基本只在本国和少数几个邻国有市场。
讲白了,他们那东西,别的国家也不要。
而完成了蜕变的中国鳗鱼,则不再拘泥于日本一地,而是远销至全球 40 多个国家。
到了 2007 年,中国已有鳗鱼养殖场 3000 多家,养殖面积约 1 万公顷,年产量约 12 万吨至 13 万吨,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二左右。
在国鳗面前,日鳗似乎只有价格还能保持领先。
但实际上,中国鳗鱼也只是在国内和日本卖得相对便宜。
在日本,中国鳗鱼保持着相对日本鳗鱼具有绝对性价比的价格,牢牢压制着日本的鳗鱼产业;
而在欧洲,由于确实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中国鳗鱼的价格完全和 “廉价” 不搭边:
出口法国的中国烤鳗最高卖到每千克 32.7 美元(2015 年数据),出口波兰的中国冻鳗最高卖到每千克 26.4 美元。
日本鳗鱼产业最大的幸运,大概就是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本国的水产养殖业,对进口水产品搞了一个配额管理制度,每年允许进入日本市场的中国鳗鱼数量有限。
如果中国鳗鱼可以对日无限制倾销,那估计日本很快就不需要有自己的鳗鱼产业了,直接就 out 了,简称 out 鳗。
毕竟,即使是对本国产品有着谜之崇拜的日本消费者,也很难拒绝价格更低、质量更好、检疫标准还更严格的中国鳗鱼。
缺钱专揍各种臭毛病。
何况,日本企业偶尔(我说的比较克制)还会在上面贴日产标签。
这下可好,连民族自豪感也一起给他们满足了。
中国鳗鱼赚到了市场,日本企业赚到了钱,只有买日本鳗鱼的消费者吃到了亏。
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6
新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遭遇,给我国的鳗鱼产业留下了一个重大教训,那就是外贸驱动的不稳定性。
一旦贸易国的政策、标准乃至国民情绪发生波动,情况就会很被动。
毕竟你真不知道某个国家又会发什么疯。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为了摆脱对日本市场的依赖,中国鳗鱼又陆续开拓了欧美市场。
到 2009 年时,曾经占到中国鳗鱼出口总量 90% 的日本,已经下滑到了 50% 左右。
但如果只有欧美市场和日本市场,鳗鱼产业依然不够稳定。
什么结构最稳定?
三角结构最稳定。
就连内裤都是三角裤最爽。
日本和欧美之外,还有着第三个巨大的市场等待开发:
内销市场。
2010 年,日本一家水产期刊上刊载了日本民间养殖鳗业协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上面给出了这样一段数据:
日本养鳗场每年所使用的日本鳗种苗约十万吨,其中本土繁育的不到 20%。为了维系产出,每年日本需要从中国进口 7.5——8.8 吨的日本鳗种苗。
还有日本鳗鱼行业的从业者表示担心:
由于中国繁育的日本鳗种苗质量太好、经验丰富,日本的养鳗业已经对此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如果中国忽然减少对日鳗苗供应,势必将对该产业造成 “致命一击”。
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就在几个月后,我国水产期刊《当代水产》上也刊载了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一篇文章。
文章分析称:
国际鳗鱼市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于鳗苗。
这个分析是对的,但实现的前提,是这些鳗苗就算不出口,也能在国内市场消化。
这时,中国的鳗鱼企业忽然发现,内销市场的开发和国际市场的主动权,实际上成为了一码事。
我国掌握着主要的鳗苗供应,而每年的鳗苗数量又是有限的。
只要内销市场能消化掉部分鳗鱼制品,这部分鳗苗缺口就可以成为拿捏国际市场的利器:
某一方积极合作,就继续供给鳗苗;
某一方不合作,就减少鳗苗供给,在当地市场出现缺口时,趁机输出我国的鳗鱼产品;
某一方政策变动,引发生产销售风险,那就干脆不玩了,把这部分鳗苗和鳗鱼产品投入内销市场。
这个操作在思路上,和其他国家在高精尖技术领域对我国进行的 “卡脖子” 策略差不多。
但这一次,是我们用一条鳗鱼苗,卡住了国际市场的脖子。
不对,应该是拴住。
也不对,勒住吧。
此时的欧洲鳗,已经因为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I 而在市场上逐渐销声匿迹,美洲鳗资源早已衰退,日本本土捕捞的鳗苗则一年不如一年,年年都要恐慌一次。
在鳗鱼人工繁育技术实用化之前,中国大陆在鳗苗上的支配地位就是无可动摇的。
而中国鳗鱼企业在后续的鳗鱼加工和品控流程上,也因为早年间日本搞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被迫修炼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备。
这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就看你争不争气了。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在同一年,有记者采访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得到了一份数据:
日本人均年消费鳗鱼量近 1000 克,中国内地人均消费鳗鱼量仅 1.6 克。
虽然那时候日料还没有那么流行,但作为世界最大的鳗鱼生产和出口国,内销发展却几乎停滞,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不光是市场潜力有待挖掘,国产鳗鱼在舆论中也几乎没有存在感。
一提到鳗鱼,大家想到的就是日料。
很少有普通消费者知道,此时的中国鳗鱼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占据了支配性地位,无论是质量还是性价比都超过日本鳗鱼。
为了打开鳗鱼的内销市场,广东省鳗鱼业协会效法日本的土用丑日鳗鱼节,从 2009 年开始举办鳗鱼美食文化节,每年一届,以推介会的形式在全国各大城市宣传鳗鱼食品。
与此同时,佛山 “顺德鳗鱼” 和江门 “台山鳗鱼” 作为广东鳗鱼的两大旗舰,相继注册为地理标准产品,开始了对内销市场的挖掘。
又过了差不多十年,国内的鳗鱼市场终于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
这时候,制约中国鳗鱼养殖加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变成了鳗鱼苗的供给不足。
鳗鱼真好吃。
2019 年冬季,那个十年前还在感慨国内消费者对中国鳗鱼 “不感冒” 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忽然很硬气地对日本媒体表示:
由于日本进口了太多鳗鱼苗,为了保障中国鳗鱼产业的发展,未来将以许可证形式限制鳗苗的对外出口。
说白了就是,当年的我你爱答不理。
今天的我,你高攀不起。
当年日本用进口配额限制中国鳗鱼制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自己也有被 “额度” 卡住的一天。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你不让我卖鳗鱼给你,那我就连鳗鱼苗也不卖给你。
你要么买我的烤鳗,要么别吃了。
我不赚你这份钱,反正我本国的市场也有足够大的容量。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2020 年,在疫情影响下,海外物流的成本猛然升高,国内鳗鱼产品的出口量迅速下降。
如果是在十年前,这对中国的鳗鱼产业绝对是一件伤筋动骨的大事,破坏力堪比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那次鳗鱼灾难。
但这一次,一个庞大的内销市场却成为了中国鳗鱼的缓冲垫。
出口量下降的同时,国内市场的销量也在迅速增长,同比增长超过了 50%。
2021 年,福建鳗鱼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量已经达到了总产量的 60%-70%,甚至超过了出口数量。
海关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我国每年平均出口烤鳗鱼 39000 吨 ——42000 吨,其中出口日本的数字为 15000 吨 ——18000 吨。
而疫情后,烤鳗内销数量增长到了 15000 吨,基本与最大的出口市场日本持平。
所有在外部市场的硬气,都来自于在内部市场的底气。
只有在不指着别人吃饭的时候,说话才敢大声。
7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几位汕头沿海居民将那一篓原本打算喂鸡鸭的鳗线便宜卖给了日本商人,到九十年代末期,鳗鱼养殖行业的狂热与惨痛;
从 2010 年以来,借助内销和鳗苗在国际市场上争夺主导权,再到疫情爆发后,在国内市场平稳落地。
鳗鱼产业这五十年来的历程,恰是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一步步攀登的缩影。
这不仅仅是一个鳗鱼游戏,更是一场国与国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艰难博弈。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每一个行业的竞争都是复杂而充满龃龉的。
对于国内的本土企业来说,市场是竞争的最前线。
但在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市场只是竞争传导的最末端。
当市场份额的变化被消费者察觉到时,这场竞争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
竞争的过程,不是简单比一比谁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低,而是我的产品要比你强十倍,才有资格同台竞技。
这就相当于我要背着一个五十公斤的负重和你马拉松赛跑,但如果我前半程跑赢了,后半程就可以把它卸下来,还可以骑着它跑。
因为我背的那玩意儿,是一辆自行车。
这是一场非对称战争,也是一场生死赌约。
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国际贸易的基础格局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际贸易中,我国的比较优势长期以来都是廉价的人工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位居全球价值链的底端。
但当既定格局中那个原本位于价值链底端的国家,终于完成了技术积累,想要跻身上游时,情况又会如何变化?
那些身为既得利益者的国家,绝不会心甘情愿让出他们的市场,也绝不舍得放弃一个可以掠夺原材料的地方。
就像十七世纪的葡萄牙人,他们会教莫桑比克人种棉花,但不会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纺织工业,甚至反过来把棉织品卖到葡萄牙本土。
在实力对比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大概率会选择用武力和威胁来对话。
如果他们没有,这不是因为他们讲文明礼貌,而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证明了自己足够强大,强大到他们付不起代价,只能用 “守规矩” 的方式竞争。
大家,手底下。
见真章。
来源:仙人 JUMP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zhangzs.com/423466.html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