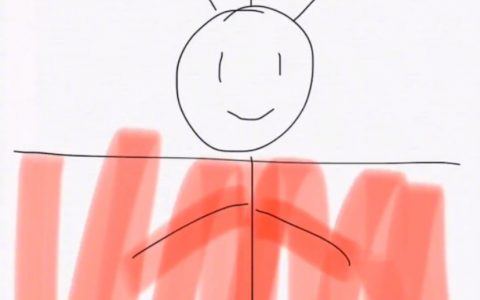从广州到我的老家开通了直达高铁,1500 多公里,7 个半小时。2024 年,春运恢复了往日的繁忙,直达的高铁票抢不到,我就先买了一张到武汉的,再转车回家。可惜临出发前,12306 发来短信,到武汉的那趟车因为冻雨、降雪的极端天气被取消。我只好补买了大年初一清晨广州到武当山机场的机票,凌晨四点多打车出发,五点多到白云机场,托运行李的队伍排起长龙。飞机在晨曦中升空,中途几次遇到气流,剧烈颠簸。空姐发给我一盒饺子,随后在动荡的机舱里蹲下来,以防摔倒。
上次回家跟父母过春节,早在 2018 年。2019 年春节,我在温暖的老挝旅行度过,那时,世界还充满欢欣和躁动。后面几年,出行不便,人心惶惶。2022 年 1 月,外婆突然离世,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我的父母终于成为了老人。爷爷奶奶去世较早,外公困在阿尔兹海默的时间迷宫里多年,先于外婆去世。外婆是父母的双亲里,最后一位入土为安的。
外婆去世前,每年冬天,父母都要把她从寒冷的县城接到有暖气的市里过冬。外婆已衰朽到行动不便,早晨下床,像下山一样艰难,下楼是完全不考虑的,对她来说,那是春暖花开回县城时才要做一次的极限运动。朝朝暮暮,她开着最大的音量,看戏曲频道,晚上七点入睡。最后电视机烧坏了,外婆也没熬过 86 虚岁的冬天。
最后几年,外婆像一尊枯萎、安谧的神像,父母在她的衰老面前,显得健壮、有用,在照顾老人的节律中,他们中年的位置得到确认。如今,兢兢业业完成了赡养义务,他们来到了人生的晚年。

而标志他们晚年生涯到来的,是年龄的节点。2022 和 2023 年,父母亲相继度过了 60 周岁生日。尽管 60 岁的妈妈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老人,但退休以后,她参加了老年大学。妈妈年轻时曾在文工团工作,会一些简单的舞蹈。老年大学的舞蹈老师希望妈妈也来代课,她犹豫了一阵,拒绝了,因为不想辛苦几十年后还要继续紧张忙碌。舞蹈老师没空时,又请妈妈去临时顶班,妈妈干脆从老年大学退了出来。活动太频密,她宁可自由一点,交钱参加了一个舞蹈班,享受做一个学员的从容。春节的街上,遇见一位阿姨,寒暄一阵,妈妈告诉我,这是她的舞友。
一年多以前,爸爸出了一次意外。他是驾驶汽车的老手,但并不熟悉摩托车。那天傍晚,临时取点东西,他借用一辆摩托,自信地出发,但刹车不灵,下坡时失控重重摔倒,失血,骨折,缝针,好在吉人天相,没有大碍,经过几个月的休养基本痊愈了。爸爸喜欢锻炼,但最近,只要一运动,他的腹部便隐隐作痛,做了一圈检查,从 CT,到肠镜胃镜,都查不出毛病。我们只能推测,也许是上次伤筋动骨后,留下的神经系统的后遗症。
那次爸爸出事住院,妈妈甚至没有告诉远在广东的我和弟弟。她的理由是,我们隔得太远,工作又忙,即便跟我们讲了,也没法回来在医院陪护,只能徒增忧虑。大半年以前,轮到妈妈腿部水肿住院。爸爸住院,陪护、送饭的是妈妈;妈妈住院,照顾她的是爸爸。两人在日常生活里拌嘴,忍耐,在患难时相濡以沫。我除了打电话关心几句,给一点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慰问金,什么忙也没帮上。父母以距离遥远为由,百般不想给我添麻烦,更加重了我的自责。
这半年来,妈妈在忙活的一件大事,是装修房子。她在好友的劝说下,买了套养老的电梯房。之前,他们习惯了住楼梯房,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她说,现在还有精力操心装修,等以后走不动了再操心,就晚了,以前住的五楼的楼梯房,还是适合年轻人爬。爸爸从机场接我,把车停在新房子的车库,我参观了装修到一半的房子和漂亮的小区。房子还是一片工地,裸露着水泥,横七竖八堆放着材料,像一个理想的胚胎,但这个理想,并不关乎盛年的人生奖励,只关于暮晚的轻拿轻放的寂寥。
新房子当然留了一间卧室给我,妈妈说我的那个房间太小,希望我不要见怪,我笑笑,没事,一年能回来住几天?春节期间,我看到留在家乡的表哥表姐表弟们,做着平凡的工作,过着充沛的人生,跑滴滴,开公交车,在小公司管财务,给银行运钞车做押运,也有人在体制内的 “好单位”,几乎都已生儿育女,含辛茹苦。
而我和弟弟,却没有如父母所愿,进入婚姻和育儿的秩序。我常常想,这既是一套象征秩序,也是一套伦理和生活实践的秩序。我更常常困惑,如果选择不婚不育,我固然有权利放弃做一个父亲,但同时也剥夺了妈妈变成祖母、变成一个真正的老人的资格。我从她疲惫又有些不安的眼神里感到的,是她作为一个老人的不自洽。我和她的距离,真的只有 1500 公里吗?我能借助高铁、飞机来抹平流动与离散的鸿沟吗?我能说清爱与孝的区别吗?我能在挂虑与自由的天平上,加上一个完美的砝码吗?
来源:南方周末 微信号:southernweekly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zhangzs.com/491911.html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